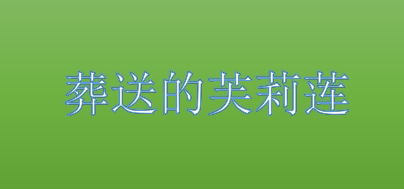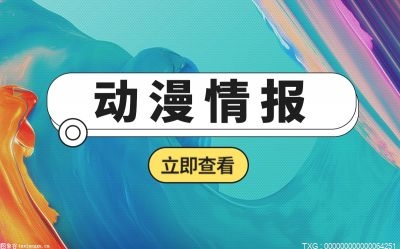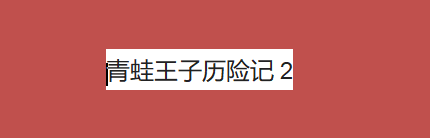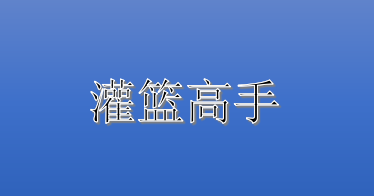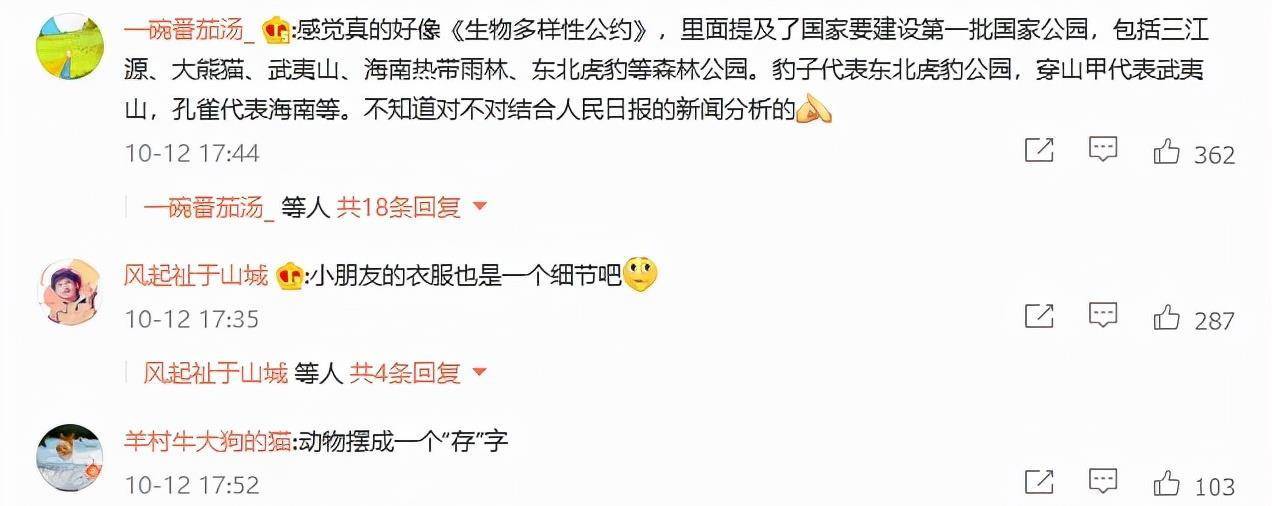冒险。如果你要和当今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赫特韦一起去前线,你别指望你将在那里遇到的任何情况是可以预测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遥远的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的大胆探险,在那里,克里斯蒂安·弗雷致力于研究被摧毁的巨大佛像。
关于他的电影拍摄的报道听起来相当冒险,然而,弗雷驳斥了任何关于他是冒险家的说法。“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他说,“虽然我可能不会回避冒险,我不寻求它。”这使他与那些“无聊而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总是需要肾上腺素的刺激。他补充道:“我对任何形式的极限运动都不感兴趣;我并不是一直在寻找刺激。”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弗雷的信条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制作者,我想探索全世界关于人类的构造。在板块相互摩擦的地方,在有震动或地震的地方,我找到了让我感兴趣的故事。”一个专注于情感中心的人,却不是个鲁莽的人?
“当然,这些通常都不是简单的故事,有时事情甚至变得很危险,”弗雷回答说,“但只有当事情变得艰难时,人才会超越自己;只有这样,这些影像才会变得重要和有趣。”如果你坚持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拍摄电影的一条戒律:“你不应该无聊!”然而,弗雷却认为他的三部主要纪录片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这件事情是一个巧合。
在拍摄《战地摄影师》的过程中,真实的危险是无法避免的。克里斯蒂安·弗雷在思考这部电影的想法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他坐在飞机上阅读一期《德国明星周刊》(Stern)时,他突然想到了这个主意,该杂志刊登了一系列纳赫特韦的照片,这些照片唤起了人们对被遗忘的阿富汗战争的回忆。这个主题完全符合弗雷对电影主题的要求:“我需要确定这个故事比生活更重要,值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继续追求。”
当导演了解到摄影师在追求真实性的过程中,希望自己不被人看到,他有了一个决定性的想法:《战地摄影师》中最有力的影像是用安装在纳赫特韦相机上的微型相机拍摄的。这种设置产生了惊人的真实性镜头。你看到纳赫特韦在工作,同时你是摄影师在战争和绝望中寻找关键时刻的目击者。这个细节说明了两件事。实现相对顺利的拍摄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是弗雷预测所有潜在发展的能力--当然,包括将成为他电影焦点的人的情绪和反对意见。更重要的是他对拍摄对象的尊重,“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一个可能不喜欢我践踏他田地的山区农民。”
关于这些图像,彼得·因德甘的贡献也不容小觑。虽然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有着弗雷所说的“迷人的友谊”。这些电影是通过一个“尊重争论”的过程产生的。弗雷说:“我倾向于明信片般的影像;而彼得提供裂缝和质地。”由于摄制组对影片的精心准备,并且摄制组尽可能地控制在小规模,所以拍摄过程不会太过干扰。弗雷经常自己负责录音,但“从不使用吊杆式麦克风--那会吸引太多的注意力。”
在《战地摄影师》中,伴随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纳赫特韦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中,试图让事情发生变化,让战争、贫穷和不公正的浪潮消退。显然,弗雷找到了他的主⼈公,但他并没有陷⼊无尽的反省。他完全是在为他的主题服务,他也把自己留在了背景中。拍摄时没有多余的艺术性,《战地摄影师》仍然是如何构建电影的典范,它逐渐接近拍摄对象的形象,巧妙地把控着观众的疑虑,暗⽰着记者职业的⽭盾。在⾳乐伴奏的帮助下,毫不费⼒地与这些可怕的影像结合在⼀起,增加了⼀种距离的元素和令⼈愉快的灵性感。
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了什么:2002年获得奥斯卡提名,在⼗⼏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战地摄影师》成为当年瑞⼠电影界的成功故事。
彼得-马蒂亚斯 盖德(Peter-Matthias Gaede),GEO杂志主编对《战地摄影师》评价道:
“我可以想象詹姆斯·纳赫特韦在拍摄时的样子,他忍受了难以忍受的事情。我以为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思考于恐怖和阴影领域的摄影师。这是位沉默寡言、孤独、绝望的记录者,但直到我看到了克里斯蒂安·弗雷的《战地摄影师》。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接近了詹姆斯·纳赫特韦。
弗雷的另一个优点是他从不抢题材的风头。他从不打扰别人,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主角身上,而是带着谨慎的同理心接近他们。否则,他永远不会成功地以足够近的距离去体验像女儿被流亡时与古巴父亲的离别;而他也永远无法将这种亲密传递给我们这些《利尔卡,米里亚姆和菲德尔》(Ricardo, Miriam and Fidel)的观众。但也因为克里斯蒂安·弗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报道者之一,他的作品将成为纪录片的经典。准确地说,它们本就如此。”
1985年,在成为世界著名图片社马格南(Magnum)的一员前不久,当时36岁的詹姆斯·纳赫特韦写下了以下文字,这是他作为战地摄影师工作的相关信条。詹姆斯·纳赫特韦:
“战争一直都有。此时此刻,战争正在世界各地肆虐。而且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战争在未来会停止存在。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文明,毁灭同胞的手段也变得越来越高效、残酷。
有可能通过摄影来终结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种人类行为形式吗?这个概念的似乎荒谬地失去了平衡。然而,正是这个想法激励了我。
对我来说,摄影的力量在于它能唤起一种人性的感觉。如果战争是一种否定人性的尝试,那么摄影可以被视为战争的对立面,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成为战争解毒剂的有力成分。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一个人为了向世界其他地方传达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承担了将自己置身于战争之中的风险,那么他就是在试图为和平进行谈判。也许这就是那些负责维持战争的人不喜欢摄影师在身边的原因。
我突然想到,如果每个人都能在那里亲眼目睹白磷对孩子的脸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或者一颗子弹的撞击造成了什么难以形容的痛苦,或者一块锯齿状的弹片是如何撕裂某人的腿的--如果每个人也能在那里亲自目睹恐惧和悲伤,然后他们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让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哪怕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更不用说成千上万了。
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在现场,这就是摄影师去那里的原因--向他们展示,伸手抓住他们,让他们停止正在做的事情,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拍摄足够强大的照片,把人们从冷漠中摇醒--抗议,并通过抗议的力量让其他人抗议。
最糟糕的是,作为一名摄影师,我觉得自己是在从别人的悲剧中获益。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每天都要考虑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让真正的同情心被个人野心所取代,我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个赌注太大了,我不可能不相信。
我试图尽我所能对这个主题完全负责。作为一个局外人,用相机拍照可能是对人性的侵犯。我为自己的角色辩护的唯一方法就是尊重他人的困境。由此被他人接受,也因此,我接受了自己。”